|
中国市场经济旗帜人物
新华社记者 轵 量
不同寻常的“人情练达”
我与柳传志只见过一面,谈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写什么东西。我当时找的话题是“转型期制度因素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基本的观点有三个:第一,按照西方的企业家理论,中国产生不了企业家,因为缺乏制度和文化的支持;第二,事实上,这20多年,中国产生了很多企业家,而且在他们身上发展出一些远比西方企业家更丰富的企业家才能;第三,因此,结论是,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即使它有多么不完整和畸形,就必然存在企业家产生的土壤。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无市场)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可能要比成熟的市场经济更需要也更能磨练企业家。只要市场经济开了一道门缝(即所谓“freedomofentrepreneurialentry”,企业进入自由),那么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就会牢牢抓住这小小的机会,把整个门撞开,趟出一条路,甚至是一条大路。我的意思是,一、中国的企业家到美国创业不一定行;二、假如是美国的企业家来中国办联想,肯定没有现在的联想做得这么好。在转型期的中国市场上,需要一些特殊的、西方管理教科书里没有的企业家才能。柳传志同意我的观点。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还没有听到我表达第二层意思——也就是由衷地赞扬联想的意思,就说:“是,我要到美国去,做不了那么大。“
在我为了写《大变局》这本书研究柳传志的时候,我发觉,这是一个在外人面前非常谦和、经常讲“我、联想什么时候有过什么问题”的人。那次交谈,他就提到,联想创业早期,和四通在同一栋办公楼办公,为了比谁挂在外面的招牌大,弄得面红耳赤。柳传志和外人的这种谈话风格,无形中是在自己“降低”自己。也正因为此,和他在一起,你绝对感受不到来自他的声名与威望的压力,柳传志“低”的这一步,让你海阔天空。这在中国的文化里,叫自谦、自抑。
我注意到,很多记者写柳传志的时候,都有一种“和他是朋友”、“很近”的情绪的流露。因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就站在了联想的立场和角度。其实,真的是朋友、真的很近吗?当然不是。但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明明不真实的感觉?这就是柳传志非常特殊的魅力。他让事实上离他很远的人都觉得很近。而更重要的是,在柳传志,这种风格并不造作,不是装给谁看的。我也相信,假如这些以为跟他是朋友的人真的有困难要麻烦他,他只要可能都是会帮助的。
柳传志的这些人情练达的行为,在同代一流企业家中极为罕见(我亲自看到和听到不止一位在名声上与柳相去不远的企业家如何在记者面前失态,因为记者的稍微为难一点的问题就大发雷霆,而且那些问题还是事实),在后辈企业家中更属凤毛麟角(他们生活的时代的价值观注定他们不再可能自我压抑,在与人交往中也决不乐意做那些利益交换不对等的事情)。
柳传志对我说:“联想跟四通学了不少东西,四通当年讲‘把铁饭碗砸了,端起泥饭碗’,让我耳目一新。四通最早成立了公关部,很重视宣传,还有和政府部门的关系。万润南对我说,公关宣传不一定是广告,如果你的企业里有国家的热点,自然会被宣传,对企业发展非常有利。联想后来坚持这样做了,但四通没做下去。”联想跟四通早已经不是一个层次(不仅是规模,更是指做企业的心态和方法),而柳至今仍在“思源”。
需要知道的是,能够把联想做到如此地步的人,其个人的大智、大慧、大勇、大谋当为必备。柳传志也是极有血气、个性极强的人。1984年,他以40岁的年龄,依然下海创业,就充分说明了他的不甘寂寞和对个人有大的期许。柳传志回首自己的创业时说过:“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么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非改不可,是一种决绝的心理硬度。在联想历史上,柳传志面对的许多困难,均属退一步即深渊的境地,非钢铁意志不足以抗衡。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人情上却又如此自谦,实在让人不能不深思。
“洞明世事”而“练达人情”
人有善根,也有弱点,并没有天生圣贤。柳传志今天的人生历练,主要还是要从他所在的外部环境来考虑。简单说,就是“世故”导致“人情”,“洞明世事”带来“练达人情”。柳传志形成今天这样的性格和接人待物的方式,与环境是分不开的。他要做大的事业,立非常之功,必须和环境有高度的和谐性,否则要么被环境拒斥而无法得到发展,要么与流俗合污而丧失高远目标。而要创造这种和谐,必须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智慧、坚韧和胸怀。用《北京晨报》记者刘书的话:“联想发展到今天,忍耐了很多很多常人无法忍耐的东西,隐藏过常理不应隐藏的黑暗,为他人背过的黑锅也历历可数。但柳传志却全做到了,保全了企业的发展,也保全了自己。”用柳的继任者杨元庆的话,柳传志有极强的妥协能力。“如果当初联想只有我这样年轻气盛,没有柳传志懂得在什么地方需要妥协的话,联想就没有今天了。”用一位联想高层经理人的话:“柳传志这么多年受过太多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审查,要是他个人真有大问题,哪怕是生活作风方面的,早就完了。别的企业老板包个情人,弄点私利问题不大,柳传志是多少人盯着的,他不能出事。他也没有出事。”
曾国藩曾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柳传志无疑是这种观念的信奉者,他多次说“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而做改革的促进者”。而要成事,用曾国藩这个清朝汉臣的话,只有“困心横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平生咬牙坚挺之诀。”自己有委屈尚且“从不说出”,就更不要说去“额上生角,触伤别人”了。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凶德致败,一是长傲,一是多言。”以曾国藩这些血泪经验来看柳传志和他的时代,大致可以明白,柳传志今日的人格性情,实在也是环境逼迫磨砺的结果(柳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时曾经说:“我在办企业的过程中,在管理上只用了30%的精力,其余70%要处理外边的一些东西。”)。牺牲一些个人的率性自由,多些忍受妥协,是为了和环境之间多些润滑,多乘顺风,使企业在已经够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之外不再另添麻烦。艰难困苦,磨练英雄,终于在玉汝于成的同时,也将一种面对外部环境的柔顺圆融之道内化为一种再难消失的个性风格——这大概就是柳传志谦和之风的源泉吧。
柳传志的这种在新一代企业家看来也许是“为难自己”、“不够自我”的一面,对于联想的发展其实还起到了另一种常常被忽视的作用。这就是,对于矫正一般中国企业容易犯的“头脑发热症”大有好处。因为妥协委屈,在内心里走的弯道多,就不会把凡事看得过于简单,像一条直线,而会有比较强的对付各种情况的心理准备,打得起持久战。这有点像高速公路的设计,过于笔直平坦则司机容易产生精神疲劳,所以高速公路的直线段都被加以限制,往往设计一些半径很大的弯道,以调节司机心理,增强安全意识。弯道费神,但出问题的几率大大少于直道。联想大的决策没有失误,与柳传志不狂不妄、从不“眼里只有自己”的风格大有关系。
企业政治观与柳传志
在中国做企业,也是在做政治,做社会。小企业有小企业的做法,大企业有大企业的做法。有积极的互动,有畸形的交易,有必须的润滑,有内心的矛盾,有彼此的利用。总之,政治是企业永远逃不脱的“地心引力”,能否处理好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对中国企业家的一大考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知名企业家,若以败局论,最惨者当为如下三人:在国企是褚时健(59岁进监狱),在私企是牟其中(58岁进监狱),在乡镇企业是禹作敏(63岁进监狱)。从大红大紫到大悲大戚,其结局实在不应只用“咎由自取”四字来概括。他们实在也是畸形体制里生下来的胎儿。这三个人,在其声名最盛时,都不亚于柳传志,甚至风头还要盖过柳传志。他们都在某个阶段被中国的政治所选择,而成为当时中国经济人物的代表。对他们的命运,直到今天,不少人还会有一丝钦佩和惋惜之情。
这三个人的失败,都不是败在才能和胆识方面,而是败在政治方面。褚时健私分公款,犯了国企的天条。牟其中吹出的泡沫太多太大(在他是引资的诱饵),一会儿是“造芯片”,一会儿是“把满洲里建成北方深圳”,一会儿是“炸喜马拉雅山引印度洋暖湿气息”,一会儿是“将雅鲁藏布江水引入黄河”。一个私营企业要干这么多国家大事,政府不警惕是不可能的,随便一个领导人批示“查一下”,南德就玩完了,因为你是经不起查的。禹作敏作为“中国首富村”的缔造者,在大邱庄一言九鼎,甚至公开说,“我去掉一个‘土’字就是皇帝。”他忘了这是谁的国家、谁在领导这个国家了。
而看看那些政治生命比较长的企业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高度注意政治安全。细分起来,大致为五类:
首先,是跟政治的大环境、大气候、意识形态的基本调子保持一致,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一位企业家告诉我:“为褚时健叫点冤屈的话我可以说,因为立足点还是为国企好,为国家好,但说中国人权不好这样的话我就坚决不说。因为这不是你企业家该说的话。”
其次,在行为方面,充分注意合法性。自己立身要正,自己先不能违法。
第三,给自己披一些“防弹衣”,造些“光圈”,找些靠山,如这代表、那委员、这捐助、那慈善一类,这样一般的政府部门就不太敢刁难你。
第四,为人低调务实,不招盛气凌人那一类的麻烦。
第五,企业对于可以决定自己命运、影响自身发展的周围方方面面的政府部门和重要官员,要舍得花时间精力,千万不可“只知埋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
以上这些做法都是“被动防御型”的“政治安全术”。在中国,一个成功的民间企业,至少必须兼具两种能力——做好企业内功的能力、在政治上防身有术的能力。当然,政治失误则企业没有前途,但如果企业首脑终日忙于在政府官员上投资,只朝上看,只朝外看,企业也必然完蛋,也就没有政治价值了。所以刘永行的观点是:“把企业做好,多交税,就是最好的政府公关。”
在企业与政治的关系中,除了“被动防御型”的“政治安全术”,有没有“积极又稳健”的“政治推动法”?所谓积极,就是争取和借助政治的力量,利用政治资源促进企业发展;所谓稳健,就是不陷入“官商勾结、违法犯罪”的泥潭。事实上也是有的,其中的方法,大体上为三种:
其一,是“交朋友”。政府官员也希望跟有思想、有实力的企业家来往,了解经济情况,这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种表现。抓住他们的这种心理,企业家可以与之建立一定的交情,取得理解和支持。例如,作为民企,陕西海星早在1995年就拿到上市指标,与公司创办人荣海的政治才能是分不开的。荣海说:“海星在陕西能够做到今天,和有一个很好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这个政治环境一部分是人家营造的,一部分是自己营造的。营造政治环境的前提,是你要有相当的学识。就政治问题,你可以和当政的人去对话,在政治方面你是很熟悉的,你对他是关心的,你对他是了解的。他们关心的不是你这个产业,严格地讲,你去和他谈电脑,他第二天就不见你了。他有可能问:‘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了,这就完了。你要能就他关心的问题和他讨论,跟他交流,最后变成朋友。这时候,他才能设身处地给你营造一个非常宽松、非常自如的环境。比如你面对一个省长,今天要贷款,明天要帮助,后天又要政策,成效可想而知。而当你能和他交流,能就他所关心的问题和他展开讨论,这种讨论他又认为是有价值的,他就开始关心你这个企业,他就开始帮忙指导你这个企业了。那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关系又是一种君子之交,而不是一种金钱关系,金钱会使人不放心你、也不会和你深交”。
其二,是“造福一方”。如果你的企业能在一个地方成为优秀企业的代表,造福当地,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有条件要求更多政治资源的支持。
第三,也是下面将要展开分析的,就是建立实业报国的远大理想(不是简单地为了个人和企业发财),并且实实在在地把这种理想灌注到办企业的过程之中(不是像牟其中式地只唱高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国际竞争的旗帜。这是一种“立乎其大”的“大政治”的企业观,而这样的企业,哪怕是民间企业,也必然得到政治的扶持。联想、华为、万向,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柳传志身上,宏观上的实业报国的“大政治”的企业观,和微观上谦和平常、注重对外沟通的“小政治”的企业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在微观层面,他比华为的任正非做得好得多)。我确信,今天如果中国的政治还需要在民间企业家中选择一个代表的话,这个人一定就是他,柳传志。
柳传志说过:“我爱看足球是因为我想看中国赢球。联想做大了,大到中国和外国较劲的时候,联想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才是我追寻的目标。”从决定做自有的联想品牌,到1993年,外资品牌的压力令中国计算机行业陷入最困难的境地,柳传志提出“坚决扛住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旗”,联想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改制的智慧
我们必须注意到,也正是因为在“政治上的正确”,联想获得了一个最大的政治支持:改制,而且是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改制。改制又加快了联想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联想和政治之间达到了良性的互动,这在中国民间企业中殊为罕见。对此,杨元庆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柳传志最大的贡献在于,摸索出了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道路。在联想体制还没有完全明确下来的情况下,柳传志就能把联想当成自己的公司干,他不等不怨,因此,他抓住了机遇。中国市场就那么几年高速发展的时机,而且,联想的发展是在外国品牌立足未稳的时候,在同行忙着或等着解决体制和产权问题的时候,联想已经做出来了。从获得经营、分配、人事三权到拥有分红权,最后到占有股权,柳传志一直在做着周密的设计,他去争,求变,积极,但不成熟的时候,他决不用强。今天我们接手的时候,联想已经是体制非常好的企业了,完全没有体制方面的后顾之忧。”
联想改制,当然不是喊喊爱国口号就行了,甚至靠联想的业绩都不能解决问题(业绩越好有时麻烦越大)。柳传志在这方面又表现出了他在具体操作上的超强能力,也就是“绕大弯,分步走”,先造小舆论,试探外界反应,然后抓住时机迅速推进。
对产权改革,柳传志早年就说过:“我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中间遇到过很多痛苦,我是怎么过来的,我很清楚。联想现在是做大了,但那是偶然因素在起作用。产权机制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应该是第一位的。”1993年,因为新老班子交替问题,联想发展遇到第一个瓶颈,第一次没有完成自己定下的任务。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柳传志再次努力,终于使中国科学院同意拿出联想35%的股份作为联想创业股,分给1988年以前进联想的创业者,兑现了“谁栽树,谁乘凉”,让创业者顺利退下,让杨元庆、郭为这样的新人走上重要岗位。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1997年,联想又将北京联想最赢利的业务注入联想香港上市公司,由部分业务上市转化为绝大多数业务在香港上市,更好地运用上市公司所拥有的认股权证的方式将员工和公司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
归结柳传志的政治智慧,首先是立意高远,非一般企业所及;其次是隐忍以行,承受常人难以承受之重;再次,是审时度势,目标坚定行动有序;最后,是积极稳健,与环境保持和谐。
我想用这样一个公式表达企业与政治的关系:100减1等于0。这个1就是政治认可。没有政治认可,企业别的方面做得再好,都很容易归于零。在如何做好企业的政治工作方面,柳传志堪为20年间难得的民企楷模。柳传志用“鸡蛋论”对此作了概括:“企业要发展,周边的环境极为重要。对一个鸡蛋孵出小鸡来讲,37度半到39度的温度最为适合。那么,40度或41度的时候,鸡蛋是不是能孵出小鸡来呢?我想生命力顽强的鸡蛋也能孵出小鸡来,但是到了100度的温度一定不行了。对企业来讲,1978年以前可能是100度的温度,什么鸡蛋也孵不出鸡来。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可能就是45度的温度,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孵出来。到1984年我们办联想的时候,大概就是42度的温度。今天的温度大概是40度左右,也不是最好的温度。因此,生命力顽强的鸡蛋就要研究周边的环境,一方面促使环境更适合,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生命力,以便能顽强地孵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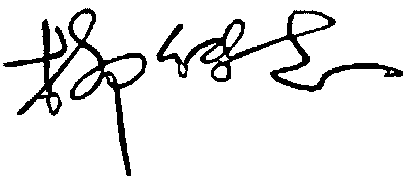


|